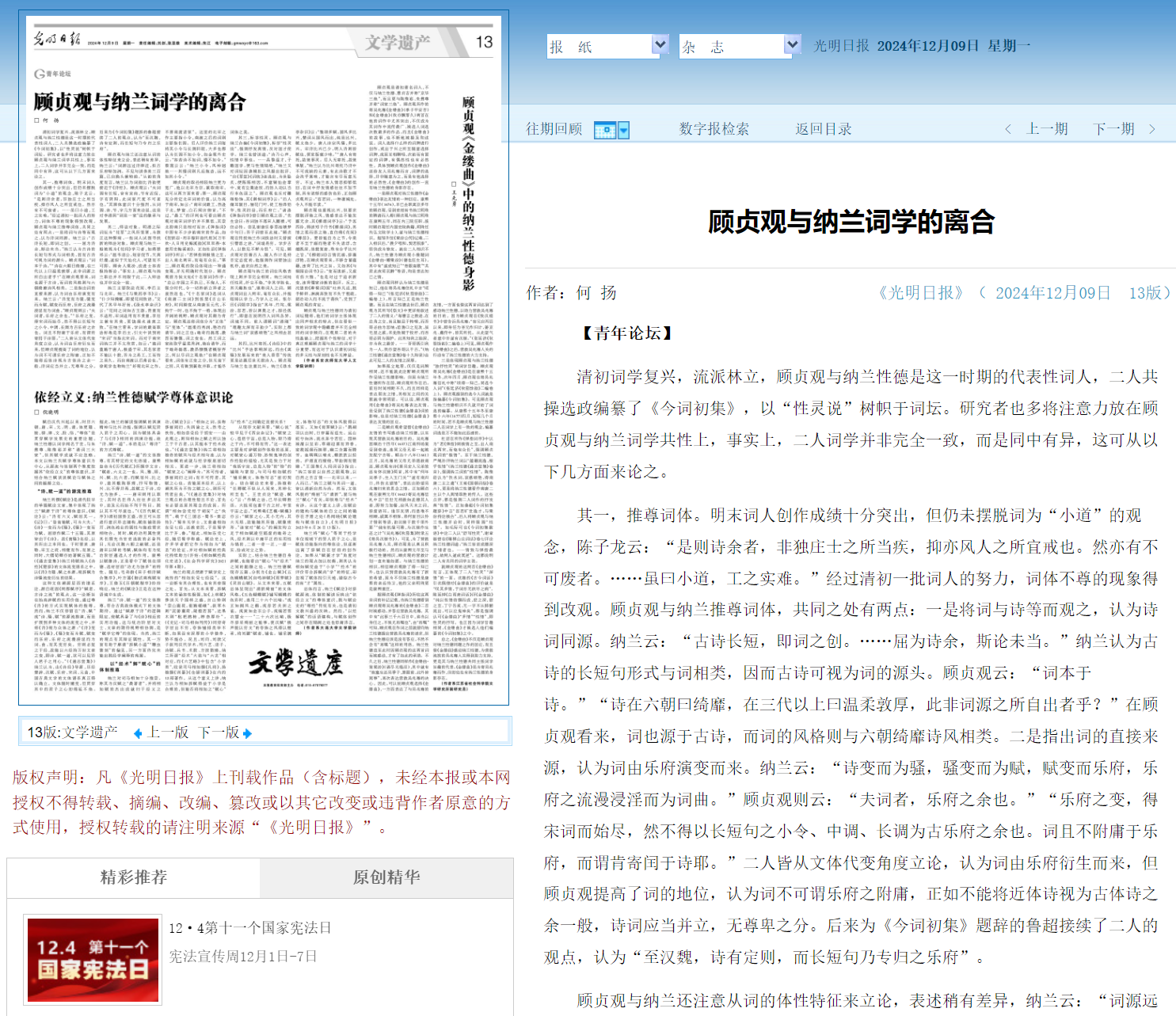
清初詞學復興,流派林立,顧貞觀與納蘭性德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詞人,二人共操選政編纂了《今詞初集》,以“性靈說”樹幟于詞壇。研究者也多將注意力放在顧貞觀與納蘭詞學共性上,事實上,二人詞學并非完全一致,而是同中有異,這可從以下幾方面來論之。
??其一,推尊詞體。明末詞人創作成績十分突出,但仍未擺脫詞為“小道”的觀念,陳子龍云:“是則詩余者,非獨莊士之所當疾,抑亦風人之所宜戒也。然亦有不可廢者。……雖曰小道,工之實難。”經過清初一批詞人的努力,詞體不尊的現象得到改觀。顧貞觀與納蘭推尊詞體,共同之處有兩點:一是將詞與詩等而觀之,認為詩詞同源。納蘭云:“古詩長短,即詞之創。……屈為詩余,斯論未當。”納蘭認為古詩的長短句形式與詞相類,因而古詩可視為詞的源頭。顧貞觀云:“詞本于詩。”“詩在六朝曰綺靡,在三代以上曰溫柔敦厚,此非詞源之所自出者乎?”在顧貞觀看來,詞也源于古詩,而詞的風格則與六朝綺靡詩風相類。二是指出詞的直接來源,認為詞由樂府演變而來。納蘭云:“詩變而為騷,騷變而為賦,賦變而樂府,樂府之流漫浸淫而為詞曲。”顧貞觀則云:“夫詞者,樂府之余也。”“樂府之變,得宋詞而始盡,然不得以長短句之小令、中調、長調為古樂府之余也。詞且不附庸于樂府,而謂肯寄閏于詩耶。”二人皆從文體代變角度立論,認為詞由樂府衍生而來,但顧貞觀提高了詞的地位,認為詞不可謂樂府之附庸,正如不能將近體詩視為古體詩之余一般,詩詞應當并立,無尊卑之分。后來為《今詞初集》題辭的魯超接續了二人的觀點,認為“至漢魏,詩有定則,而長短句乃專歸之樂府”。
??顧貞觀與納蘭還注意從詞的體性特征來立論,表述稍有差異,納蘭云:“詞源遠過詩律近,擬古樂府特加潤。不見句讀參差三百篇,已自換頭兼轉韻。”從韻的角度而言,納蘭認為詞韻比詩韻更接近于《詩經》。顧貞觀云:“夫詞調有長短,音有宮商,節有遲促,字有陰陽,此詞家尺度不可紊也。”其辨體意識十分強烈,從詞調、音、節、字幾方面來論說,這是對李清照“別是一家”說的繼承與發展。
??其二,師法對象。明清之際詞壇為“花草”之風所籠罩,為撥正這種弊病,一些詞人試圖尋找新的師法對象。顧貞觀與納蘭一般被視為《花間》學習者,如蔣景祁云:“溫韋諸公,短音促節,天真爛漫,遂擬于天仙化人,可望而不可即。顧舍人梁汾、成進士容若極持斯論。”事實上,顧貞觀與納蘭取徑并不局限于此,二人師法也并非完全一致。
??納蘭主要取法花間、李后主與北宋。納蘭《與梁藥亭書》云:“仆少知操觚,即愛花間致語。”交代了其早年好尚。《淥水亭雜識》云:“花間之詞如古玉器,貴重而不適用,宋詞適用而不貴重,李后主兼有其美,更饒煙水迷離之致。”在納蘭看來,學詞的最高取法標準是李后主,引文中談到的“宋詞”當指北宋詞。而對于南宋詞納蘭并不太欣賞,如云:“填詞濫觴于唐人,極盛于宋,其名家者不能以十數,吾為之易工,工而傳之易久。而自南渡以后弗論也。”徐乾學也稱納蘭“好觀北宋之作,不喜南渡諸家”。這里的北宋之作主要指小令,南渡之后的詞則主要指長調。后人評價納蘭詞每將其小令與長調軒輊,大多也都認為長調不如小令,如金梁外史云:“容若詩不如詞,慢不如令。”蔡嵩云云:“納蘭小令,風神迥絕……其慢詞則凡近拖沓,遠不如其小令。”
??顧貞觀的取徑相較納蘭更為寬廣,他以北宋為宗,兼取南宋。這可從兩方面來看:第一,顧貞觀充分肯定北宋詞的價值,認為高于南宋,如云:“南宋詞最工,然遜于北,夢窗、白石聞言俯首。”不過,“最工”的評判也可看出顧貞觀對南宋詞評價并不算低,其崇北抑南只是相對而言。《彈指詞》中即有不少步韻南宋的作品,如《賀新涼·用辛稼軒韻代別》《萬年歡·人日用史梅溪韻》《雙雙燕·本意用史梅溪韻》。正如杜詔《彈指詞序》所云:“若彈指則極情之至,出入南北兩宋,而奄有眾長。”第二,顧貞觀的取徑體現出一種通變觀,并無明確時代劃分。顧貞觀曾為侯文燦《十名家詞》作序:“總讓亦園之不執已,不徇人,不強分時代,令一切矜新立異者之廢然返也。”《十名家詞》選詞從《南唐二主詞》到張埜《古山樂府》,時間跨度從南唐至元代,不拘于一時,也不拘于一格,體現出開闊的視野,顧貞觀對其頗為肯定。顧貞觀還將詞體分為“正體”與“變體”:“溫柔而秀潤,艷冶而清華,詞之正也;雄奇而磊落,激昂而慷慨,詞之變也。然工詞之家徒取乎溫柔秀潤,艷冶清華,而于雄奇磊落,激昂慷慨者概皆棄之,何以盡詞之觀哉?”在顧貞觀看來,詞體有正變之分,但無高下之別,只有做到兼收并取,才能盡詞體之美。
??其三,標舉性靈。顧貞觀與納蘭合編《今詞初集》,標舉“性靈說”,強調抒發真情,反對逞才使學。納蘭也曾談道:“詩乃心聲,性情中事也。……昌黎逞才,子瞻逞學,便與性情隔絕。”納蘭又對詞壇因襲模擬之風提出批評,“自《草堂》《詞統》諸選出,為世膾炙,便陳陳相因,不意銅仙金掌中,竟有塵羹途飯,而俗人動以當行本色詡之”。顧貞觀也反對雕琢粉飾,其《澣桐詞序》云:“后人傭耳僦目,儷花門葉,徒工粉澤鉛華,性靈汩沒,而樂府亡。”諸洛《彈指詞序》曾引顧貞觀之語,“先生嘗曰:吾詞獨不落宋人圈,可信必傳。嘗見謝康樂春草池塘夢中句曰:吾于詞曾至此境。”顧貞觀在傳授納蘭作詞技法時又曾援引曹溶之語,“詞境易窮。學步古人,以數見不鮮為恨”。可見,顧貞觀對因循古人、隨人作計是持否定態度的,他強調作詞要獨出機杼,追求自然之美。
??顧貞觀與納蘭的詞在風格表現上則并非完全相同。納蘭詞純任性靈,纖塵不染,“非其學勝也,其天趣勝也”,堪稱詞人之詞。顧貞觀詞出入兩宋,奄有眾長,并能熔鑄以學力,乃學人之詞。張爾田《詞莂序》指出“其年、竹垞、梁汾、容若,皆以淵奧之才,辟徑孤行”,即意在說明四人詞風各異,詞境不同。前人謂顧詞“清剛”“理趣太深而豐韻少”,實際上都與納蘭詞“哀感頑艷”之風相去甚遠。
??其四,比興寄托。《詩經》中的“比興”手法影響深遠,而由《離騷》發展而來的“美人香草”傳統更是沾溉后世無數詩人。顧貞觀與納蘭也注重比興。納蘭《淥水亭雜識》云:“雅頌多賦,國風多比興,楚詞從國風而出,純是比興,賦義絕少。唐人詩宗風騷,多比興。宋詩比興已少,明人詩則皆賦也,便覺版腐少味。”“唐人有寄托,故使事靈。后人無寄托,故使事版。”納蘭認為比興寄托乃詩中不可或缺的元素,有此詩歌才不會淡乎寡味,才能言有盡而意無窮。不過,納蘭本人情思抑郁低回,在詞中抒發情感往往不加節制,具有濃郁的感傷色彩,正如顧貞觀所云:“容若詞,一種凄婉處,令人不能卒讀。”
??顧貞觀也重視比興,但要求擺脫浮艷之風,情感表達不能發露無余,其《柳煙詞序》云:“予客西泠,得讀鄭子丹書《柳煙詞》,其情之柔而語之艷,直仿佛《花間》《樽前》。要皆能自為之節,令柔者不至于溺而艷者不失諸浮,含蘊既深,體裁復密,殊有合乎比興之旨。”《柳煙詞》言情沉溺,辭藻浮艷,在顧貞觀看來,不夠含蓄蘊藉,違背了比興之旨。又如其《與栩園論詞書》云:“變而謀新,又慮有傷大雅。”也是對過于追求新變,違背儒家詩教的批評。反之,沈堡的《澣桐詞》因“吐棄凡近,脫手鮮妍,淋漓奔放而不失于粗疏,韶冶動人而不流于蕩佚”,受到了顧貞觀的肯定。
??顧貞觀與納蘭性德同為清初詞壇健將,他們的詞學主張體現出同聲相求的特點,但在看似一致的詞學觀中隱藏著并不完全相同的詞學傾向,在觀照二者的共性基礎上,把握其個性特征,對于真正理解顧貞觀與納蘭的詞學十分重要,而這對于認識清初詞壇的多元性與深刻性也不無裨益。
??(作者:何 揚,系安慶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)
來源:【光明日報】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4-12/09/nw.D110000gmrb_20241209_1-13.htm

 安徽安慶菱湖南路128號
安徽安慶菱湖南路128號 郵編:246011
郵編:246011 安徽安慶集賢北路1318號
安徽安慶集賢北路1318號 郵編:246133
郵編:246133